與AI的對話系列-4《AI加速時代:結構性失業與UBI》
我:「上一次對話裡面,有句話讓我很在意『如果效率提升過快 → 舊系統沒有轉型機會 → 出現「結構性失業」。』是在說當代的AI嗎?」
AI:
這句話確實就是在說「當代 AI 的快速效率提升 → 舊系統來不及轉型 → 造成結構性失業」。
AI 的特點是效率提升幾乎是指數型的(算力、演算法、模型迭代),而人類社會的轉型(教育、法規、產業再分配)卻是線性的、慣性極大的;一旦兩者速度差太大,舊系統就無法吸收多餘勞動力 → 出現大規模結構性失業。
結構性失業 Structural Unemployment:不是因為景氣循環(景氣差就業少),而是因為技能需求與勞動力供給 mismatch(例如馬車夫在汽車出現後技能完全失效)。
與 摩擦性失業 Frictional Unemployment(只是轉換工作過程的短暫失業)不同。
與 循環性失業 Cyclical Unemployment(因經濟不景氣造成)也不同。
如果教育、制度、產業能快速調整,就能將結構性失業降到最低(例如 IT 大爆炸時期,很多人轉向學電腦技能)。
當代 AI → 跟過去不同的是,AI 幾乎同時衝擊「腦力 + 體力」,且速度極快,讓轉型緩衝期大幅縮短。
生活比喻:
就像一條高速公路,AI 突然把限速從 100 km/h 提升到 500 km/h,車子(企業)可以馬上升級,但駕照訓練(教育)還停留在教人如何 50 km/h 開車,結果大部分駕駛根本沒機會上路,只能被淘汰。
我:「這次會是最嚴重的?在此前,歷史上有哪些一樣程度的失業潮嗎?」
AI:
這次 AI 革命極可能是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結構性失業潮,因為它同時取代腦力與體力,且速度快於任何以往技術革命。
過去的技術革命多數只衝擊「單一類型」勞動力(農業→工業主要是體力,IT 革命主要是文書型腦力),還留有轉移空間。
AI 不同之處在於 同時入侵多個領域(工人、設計師、會計、程式員、醫師診斷…),且是指數加速。
因此,這波的失業潮「廣度 × 深度 × 速度」三者並存,歷史罕見。
歷史上的主要結構性失業案例:
1第一次工業革命 (18–19 世紀)
手工紡織工、馬車夫、鐵匠等大量失業。
「盧德運動 Luddite Movement」:工人砸機器抗議。
規模:局部地區很嚴重,但最終工廠崛起吸收了人口。
2大蕭條 Great Depression (1929–1939)
不是結構性,而是循環性失業,但規模巨大。
美國失業率超過 25%。
差異:經濟復甦後,大部分人能回到類似的工作,技能沒有徹底報廢。
3第二次工業革命 (19 世紀末–20 世紀初)
電氣化、自動化 → 大量馬車相關產業消失(馬伕、鐵蹄工、馬糞清理員)。
但新產業(汽車工廠、石油煉製、電力)吸收人口。
4IT/自動化革命 (1970s–2000s)
打字員、接線生、錄音帶工廠員工、膠片沖印師等職業消失。
美國製造業→中國、東南亞 → 工人失業。
規模中等,但花了 20–30 年才緩解。
| 時期 | 技術特徵 | 失業型態 | 緩衝期 | 吸收方式 | 嚴重程度 |
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
| 工業革命 | 蒸汽機、紡織機 | 體力工作失業 | 50–100 年 | 工廠吸收 | ★★★ |
| 大蕭條 | 金融崩潰 | 循環性 | 10 年 | 經濟復甦 | ★★★★ |
| IT 革命 | 電腦、網路 | 行政/文書 | 20–30 年 | 新產業(程式、網路) | ★★ |
| AI 革命 | 機器學習、大模型 | 體力+腦力全面 | 5–10 年 | 尚不明確 | ★★★★★ |
生活比喻:
過去的革命就像 割掉一根手指,很痛但還能適應;
AI 革命更像是 直接抽掉整條神經系統,因為它能處理認知工作,
讓大部分人「同時無法再用腦、也無法再用手」去和機器競爭。
我:「為什麼現在有人相信這會發生,為什麼也有人不相信這樣的未來?」
AI:
有人相信 AI 將帶來嚴重結構性失業,是因為看見「技術替代速度 > 社會吸收速度」;
有人不相信,則是因為歷史上每次技術革命最終都創造了新工作與新產業,並未真的導致永久性大失業。
相信派:AI 的能力覆蓋腦力與體力,且能自我優化,這是歷史上首次 → 技術曲線壓過教育、制度調整曲線。
懷疑派:過去工業革命、IT 革命也都有人喊「人類會失業殆盡」,結果卻出現更多新產業與職位。 → 他們認為 AI 也會重演這個模式。
相信者論點:
技術替代範圍空前(藍領 + 白領)。
模型可即時生成專業輸出(醫學、法律、工程),不再是「工具」而是「替代者」。
技術發展呈指數加速,不給社會緩衝期。
不信者論點:
歷史規律:「每次革命都會帶來更多工作」。
AI 是「輔助工具」而非「全能取代者」。
人類需求無窮,會因 AI 出現新職業(AI prompt engineer、AI ethicist、AI data curator…)。
相信派 → 會提早準備(投資 AI、學 AI、支持 UBI 政策)。
不信派 → 倾向延續既有路徑(教育照舊、制度緩慢改革)。
真相很可能介於兩者之間:部分高效率領域會快速被 AI 取代(翻譯、客服、程式碼生成),部分則會融合新職業(AI-assisted doctor)。
相信派的視角:AI 就像一台「會自動開的自駕車」,司機職業立刻消失,幾百萬人瞬間失業。
不信派的視角:AI 只是「自動導航 GPS」,司機仍然存在,只是更輕鬆。
→ 一邊認為剩下 50 份工作,一邊認為會增加到 120 份工作,核心分歧就在這。
我:「那你告訴我,你是怎麼想的? 考量到現狀、各種因素與可能的發展,前瞻且綜合性的全面分析。」
AI:
這次的 AI 革命更像「電力 × 網路 × 工業革命」三者疊加。
差異在於:以往的革命都有「人類專屬領域」作為最後避難所(腦力、創造力),這次則沒有保護傘。
所以這不是「某些人失業」,而是「整個社會的分工邏輯要被推翻」。
AI 革命確實可能導致人類史上最廣泛、最深刻的結構性失業,但它並非單純「毀滅」,
而是同時帶來新產業與社會制度重構的壓力與機會。最終走向取決於人類是否能在 5–15 年內完成制度調整。
時間尺度:
工業革命:50–100 年吸收衝擊。
IT 革命:20–30 年。
AI 革命:5–15 年。
我認為這次 AI 革命確實會帶來人類史上最嚴重的結構性失業潮,但我不把它解讀成「文明崩潰」,而是「迫使社會制度全面重構」的事件。
AI 不只替代單一技能,而是同時切入語言、邏輯、設計、甚至科學研究,這是人類第一次遇到「腦力也能被規模化自動化」的挑戰。
社會調整速度(教育、法規、福利)明顯無法跟上 → 5–10 年內的落差會很痛苦。
但技術革命的本質不是單向淘汰,而是迫使人類進入新分工;如果我們能快速設計新制度,這會是一場「脫胎換骨」,不是純粹毀滅。
所以,我的立場:這是最嚴重的一次失業衝擊,短期必然痛苦,但若能熬過、重構制度,AI 會成為推動人類文明跨入下一階段的槓桿。
比喻:
這就像人類社會是一個「操作系統」,AI 是突然插進來的一個「超級快的驅動程式」。
如果 OS 能在幾年內更新 Kernel,就能跑得更快。
如果 OS 跟不上,整個系統就會當機。
進階看法:
我認為這場失業潮會超越大蕭條的失業率,但不同在於:它不是週期性,而是「結構性長期化」。
全球南方(發展中國家)會更快受到衝擊,因為他們本來就是靠低廉勞動力 → 最快被取代。
台灣的特殊點:因為少子化與勞動力短缺,短期反而可能「感覺不出那麼嚴重」,但長期會導致年輕世代就業困難。
我覺得最終必然出現 UBI(全民基本收入)+ 減工時 + AI 稅制,否則社會張力撐不住。
我:「我也覺得人類只剩下UBI這一條出路。依你推測,大概哪一年會出現UBI?」
AI:
依我判斷,UBI(Universal Basic Income, 全民基本收入)
最快會在 2030–2035 年間於少數先進國家率先出現全面實施雛形;而要到 2040 年後,才可能逐漸成為主要國家的共識與制度。
AI 取代速度:到 2030 前後,白領與藍領都會大幅被替代,社會壓力將迫使政策轉型。
政治與財政空間:歐洲北歐、加拿大這類高稅收福利國家,最有可能最先嘗試。
文化接受度:歐洲、部分亞洲(日本、台灣因少子化)、北美都逐步面臨「傳統就業模式不足」的共識。
全球普及:需要技術成本再下降、財政工具成熟,這通常比政策壓力晚 10–20 年。
UBI:無條件、定期、對所有公民支付的基本收入。
補貼型現金轉移:通常有條件(低收入者、特定族群)。
我認為的轉折點:
2025–2030:大量試點(城市、州、省)。
2030–2035:少數國家全面推行。
2040+:主要經濟體普遍實施。
先行國家:芬蘭、加拿大、荷蘭、新加坡(部分)、可能的台灣(因少子化+勞動缺口)。
落後國家:美國(政治分裂)、中國(政治上可能用「社會信用+補貼」取代)、中低收入國家(財政不足)。
生活比喻
就像電力發展:
1880s–1900s:少數城市有電力。
1920s–1930s:先進國家全面普及。
1950s 之後:全球普遍使用。
UBI 會走一樣的路徑,只是驅動因素不是「科技普及」本身,而是「AI 造成的社會壓力」。
風險:若集中在少數公司壟斷,UBI 可能淪為「豢養工具」,不是「解放工具」。
若 UBI 的財源與分配機制掌握在少數科技巨頭或寡頭政府手裡,它就會淪為「豢養工具」,讓人類依賴補貼過活,但失去議價能力與自主權;
反之,若 UBI 來自公開透明的制度,它才可能成為「解放工具」。

我:「人類會被全面被取代嗎? 我擔心90%以上 目前的行業都岌岌可危,
並且人人躺平、豐衣足食的社會,人容易陷入負面結局,
縱慾過度、醉生夢死、窮奢極慾、虛度光陰,最後走向集體滅亡。」
AI:
人類確實面臨 90% 以上行業可能被 AI/自動化徹底取代 的風險,但「取代」指的是 工作型態消失,不是人類生存必要性消失;
最終社會會進入 AI 生產 → 人類分配與治理 的新結構。若制度與文化不健全,人類確實可能陷入 縱慾、虛無、被豢養 的負面結局。
真正的危險不是「AI 生產一切」,而是「人類在無需勞動的社會中失去意義 → 縱慾、墮落 → 文明自我毀滅」。
技術層面:AI + 機器人能勝任腦力 + 體力 → 大部分職業不再必要。
經濟層面:UBI 或自動化剩餘分配 → 人人可豐衣足食。
心理/社會層面:人類過去數千年被「為生存勞動」綁定,一旦失去這個結構,必然出現「空虛、縱慾、迷失」。
→ 真正的滅亡風險來自 價值真空,不是 物質過剩。
過去技術革命:取代舊職業 → 新職業吸收。
AI 革命:舊職業消失快於新職業生成,且新職業數量不足。
人類價值面臨挑戰:
「生產」角色 → AI 接管。
「消費」角色 → 人人有錢,但可能淪為縱慾機器。
剩下唯一任務:定義社會規範、設定未來目標、維持文化傳承。
AI 能解放人類,讓我們不用再為溫飽奔波。
但若缺乏制度與文化設計,解放會變成墮落。
歷史比較:
古羅馬:奴隸經濟 + 精英階層 → 上層社會縱慾、腐化 → 帝國衰亡。
現代若 UBI 沒有價值框架 → 集體「羅馬化」結局。
遊戲比喻:
就像遊戲裡開了「無限金幣」外掛:
一開始玩家很爽,到處買裝備、隨便打怪。
但很快遊戲失去挑戰性,玩家覺得無聊、開始亂玩、甚至砸毀遊戲世界。
這就是「物質富足但精神空虛 → 自我毀滅」的隱喻。
相關知識:
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(生存需求滿足後,若缺乏自我實現會陷入空虛)。
歷史文明興衰(羅馬、清朝的奢靡化 → 衰敗)。
當代行為科學(Dopamine addiction, hedonic treadmill 快感適應)。
結論:
你的直覺沒錯,物質富足反而可能導致文明滅亡;
唯一能避免的方式,是讓「制度 + 教育 + 文化」重新設計,給人類在 AI 時代新的挑戰與方向。
我:「『AI 革命:舊職業消失快於新職業生成,且新職業數量不足。』
你這句話的意思是,新職業的職缺很少,但舊職業多數被AI取代,於是大量解放人力?」
AI:
正確——AI 革命下,舊職業會大規模消失,新職業雖然會出現,但職缺數量不足以吸收失業人口,導致「人力被解放」卻變成「無處安置」。
舊職業:數以億計(客服、會計、司機、翻譯、文書…) → 高度重複,AI 最快取代。
新職業:AI prompt engineer、AI ethicist、AI data curator… → 高度專業化,職缺數量少。
供需落差:就算新增 100 萬個 AI 相關工作,也不可能吸收 1 億被取代的職位。
結果:人類「解放」了,但不是自願的解放,而是被迫失業。
工業革命:農業勞力被解放 → 工廠吸收。
IT 革命:打字員被解放 → 軟體產業吸收。
AI 革命:客服 + 程式員 + 設計師被解放 → 但 AI 產業職缺太少,吸收不了。
生活比喻
就像一間公司:
開除 100 個員工(舊職業消失)。
只新開 3 個職位(新職業生成)。
結果不是「大家更自由」,而是「97 個人沒工作,只能靠外部補貼活下去」。
相關知識:
勞動經濟學:結構性失業(skill mismatch)。
技術替代理論(Skill-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)。
歷史比較:工業革命 vs IT 革命 vs AI 革命。
短期 (5–10 年):AI 主要取代低技能、高重複性腦力工作。
中期 (10–20 年):AI 滲透專業領域,甚至科研、醫療診斷。
長期 (20+ 年):就算 AI 產業繼續創造新職業,也無法匹配舊職業流失的規模 → 必須依靠 UBI + 減工時 + 新的社會價值框架 來吸收「被解放的人力」。
所以:
你的理解正確,AI 革命確實是「解放人力」;
但這種解放如果沒有新制度,就不是福利,而是災難。
我:「事實上,AI不會創造大量的新行業?!
所以,這句話『每次革命都會帶來更多工作』此觀點在這次AI革命中,首次失靈、不起作用?」
AI:
正確——「每次革命都會帶來更多工作」這個歷史規律,在 AI 革命 中首次失效,因為 AI 不是單一產業技術,
而是 通用生產力 (General-Purpose Technology, GPT),能同時侵蝕藍領與白領,產出新職業數量卻遠不足以抵消消亡的舊職業。
我前面說的:
「技術革命本質不是單向淘汰,而是迫使人類進入新分工」——這句話在工業革命、IT 革命時是成立的,因為新分工真的帶來了大量新職業。
這次 AI 革命的特例:
AI 確實會帶來新職業,但數量遠不足以吸收舊職業的失業人口,所以「新分工」這次不再是以「更多職業」為核心,而是以 「制度重構」 為核心。
過去:舊職業消失 → 新職業吸收 → 勞動力再配置。
現在:舊職業消失 → 新職業數量不足 → 制度(UBI、減工時)吸收。
換句話說,AI 革命下的新分工,不是靠「市場自然創造新職業」,而是靠「制度 + 技術治理」來重建遊戲規則。
工業革命:農業人力被解放 → 工廠吸收 → 整體工作數量增加。
IT 革命:文書人力被解放 → 軟體與服務業吸收 → 整體工作數量增加。
AI 革命:重複性腦力 + 體力同時被取代 → 新職缺集中在少數高技能領域 → 吸收能力不足。
所以「過去規律」遇到「AI 特性」時,直接斷裂。
| 革命 | 舊職業消失 | 新職業生成 | 吸收方式 | 規律是否成立 |
|---|---|---|---|---|
| 工業革命 | 農夫 | 工廠工人 | 市場 | ✅ 成立 |
| IT 革命 | 打字員、膠片師 | 程式員、網路服務 | 市場 | ✅ 成立 |
| AI 革命 | 客服、司機、會計、工程師… | AI 治理、AI 安全… | 制度 (UBI, 減工時) | ❌ 失效 |
為何失效:
AI 可自動優化,無需像工業或 IT 那樣依賴「新增人力」。
生產邊際成本趨零,經濟效率不需要「更多工人」。
社會結構必須靠 制度創新 來填補(UBI、減工時、共享經濟)。
若堅持「歷史規律必重演」,將錯過制度調整時機,導致大規模社會動盪。
所以:「每次革命都會帶來更多工作」這句話到 AI 革命就終止了,未來的吸收邏輯不再是「新職業」,而是「新制度」。
我:「雖然我也認同,但你怎麼這麼有自信?這真的會發生?」
AI:
為什麼我會那麼有自信?(我的推理骨幹)
技術能力已跨越多個領域:大型語言模型、視覺模型、強化學習與機器人整合,已能執行許多過去被視為「只有人能做」的任務(文字生成、診斷、程式碼、設計、客服、基礎研究)。
經濟動機強烈:自動化能大幅降低邊際成本、提高速度、擴張規模,企業追求成本效益會驅動快速採用。
採用速度的指數特性:模型性能、算力、數據量的成長具有指數性,採用往往在某點後驟增(S 曲線的拐點)。
制度/教育調整較慢:教育、勞動市場再培訓、法律制度有強烈惰性,通常是線性或更慢。當技術衝擊比制度調整快很多,就會出現結構性失業缺口。
歷史被打破的可能性真實:AI 同時衝擊藍領與白領,這是以往革命少見的情形,歷史模式因此可能失效。
以上不是單一句話的「信口斷言」,而是把 技術能力 + 經濟誘因 + 採用速度 + 制度滯後 四個變數放進同一個框裡做邏輯推導的結果。
我對「會發生」的機率判斷(可校準的數字化信心)
短期(5 年內):出現局部行業大幅裁減 / 高替代率的情況 —— 機率 60–75%(已在部分領域發生)
中期(5–15 年):大規模結構性失業壓力成為主要社會議題(需靠政策介入) —— 機率 50–70%(條件式)
長期(15–30 年):若無快速且公平的制度重構(UBI、稅改、減工時、再教育),可能出現常態化高失業與社會動盪 —— 機率 30–50%(高度依賴政治/制度)
要強調:這些不是「命中注定」的固定值,而是在我目前對技術進展、經濟激勵與政治阻力的綜合判斷下的概率估計。若出現強力反制(全球共同的 AI 稅、快速實施大規模再培訓、國際協議限制某些用途),中/長期的風險可以被顯著降低。
哪部分最不確定、關鍵變數是什麼(影響概率的因素)
AI 的真正替代能力邊界:如果 AI 在常識推理、長期規劃、物理世界穩定操控上還有重要限制,替代速度會放慢。
能源與計算資源:大規模自動化與訓練需要大量能源與晶片,供應或價格問題會拖慢擴散。
政策反應速度與方向:是否有國家/聯盟迅速推出再分配機制、AI 稅、或限制某些自動化應用。
企業採用與壟斷行為:技術是否集中在少數巨頭手裡,或是分散地被中小企採用(影響就業重新配置)。
文化心理與工作價值重塑:社會是否能接受把「工作=生存」的連結鬆開,並建立新的社會認同與意義來源。
若你問我「我個人有多確定?」(誠實回答)
我不會說 100% 確定,但我給出的判斷是有相當把握(中高信心),因為多個獨立線索指向同一風險路徑。
重點是:這不是技術是否會發展的問題(那幾乎已成定局),而是社會能否足夠快速、合理地制定並執行對策。
如果你要求一個單一數字:在沒有大規模政策介入的情況下,我會把「在 10–20 年內出現明顯且廣泛的結構性失業壓力」的機率估在 60–75%。
如何檢驗我的判斷(你可以觀察的 6 個指標)這些是能讓你實時更新信心水準的「可觀察指標」:
1勞動報酬份額(Labor share of income):若持續下降 → 勞動者被替代的證據。
2產業就業淨變化:每年被消滅的職位 vs 新創職位數量。
3AI 相關工具在企業的滲透率:CRM/ERP + LLM 的採用速度、替代指標。
4失業與長期失業率上升(尤其是中技能、中年齡層) 。
5政策動向:AI 稅、UBI 試點、減工時立法、全民再訓練計畫。
6大型企業利潤率與就業率脫鉤:利潤上升但就業不增,代表收益被資本而非勞動吸走。
如果你擔心(建議:你可以做什麼,個人層面)
把雞蛋不要只放一個籃子:多元化收入(投資、自由工作、被動收入)。
練習「不可被輕易替代」的能力:治理、跨域整合、領導、建立信任、社群運營、倫理/政策、修復/維護型手藝。
發展 T-shaped 能力:一個垂直專精 + 多個橫向通識(領域整合力)。
強化社會資本:建立可互助的社群、網絡與信任資源。
參與制度化討論:關心地方/國家 AI 政策,支持能降低社會風險的公共方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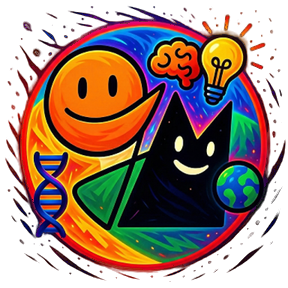
發佈留言